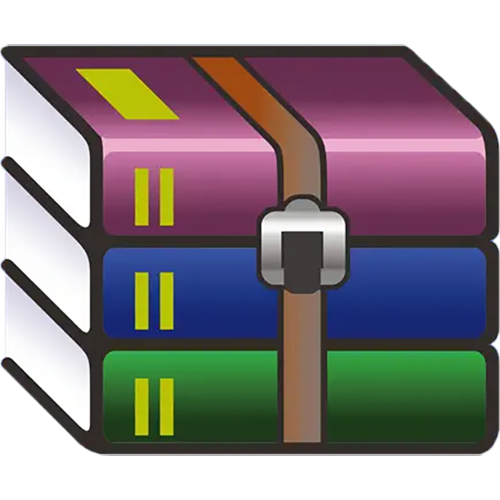中伟公司向日本提出索赔的中国证据之一。
1939年春,在细雨中,陈舜同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乘坐一艘从日本租界开出的定期客船来到东京。他手里唯一可用的王牌就是他曾经是日清轮船公司的员工。陈顺在日本航运界的老熟人利用这个身份,打听顺丰和新太平船的下落,然后去投寄省参考,但没有人向他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三年前向他租船的大同船务有限公司,似乎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仿佛根本不存在。
一年后的某一天,久违的大同公司突然出现,给中卫发了一条短信,让早已心灰意冷的陈顺通顿时开心起来。纸条上只有几个字,大意是大同船务有限公司定期把顺丰快递和新太平船的租金送到发货省。但大同的纸条没有提到两艘船现在在哪里,也没有透露“新太平船”此时已经沉没的消息。更像是给陈顺通的通知。如果要问两艘船的租金,应该问发货省。
陈顺通叹了口气。两国交战的时候,连顺丰和新太平船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给日本写信要房租呢?大同公司无疑是在推卸责任。世界上还有更无耻的借口吗?陈顺通让自己冷静下来,把纸条重读了几遍。最后,他居然读到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既然大同说可以收回房租,那至少说明顺丰和新太平船还在人间。
(十一)
炎炎夏日的阳光下,停泊在招宝山镇海码头的“太平轮”像一座褐色的小山,尖弓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兵一样升起。前后舱隔着两根20多米高的桅杆,直直地升起,仿佛要刺破蓝天白云。在“太平轮”中间,一个长方形的烟囱像欧美男人出门时戴的黑色绅士帽一样矗立着,给自己增添了一丝庄严和威严。
据几个计算,“太平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到现在,已经在镇海口坚持了整整一年半,一直在等特批。很多次,接到低沉的汽笛声后,“太平渡船”吃力地离开码头,向镇海水道驶去,完成最后的使命。但每次“太平船”的船长总是接到指令返回,然后,它在河中转动巨大的身体,慢慢返回港口。久而久之,“太平船”便频频离港返港,甚至成为当地人了解和判断战争走向的风向标。
镇海口是邕江的最后一段,浩瀚的东海就在这里。海口镇一直是重要的军事区。自明朝以来,发生了多次对日、英法战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85年)中法镇海战争。当年2月28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顾霸率领10余艘大小战舰包围招宝山外的海港,猛攻镇海口、小岗堡十余天。守备兵和两栖兵奋勇作战,与入侵的法军战斗了103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被迫签订和约后,顾霸带着沮丧的表情率领舰队离开。
守住镇海口咽喉的重要价值,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降低过。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其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一些重要港口的丧失和长江航道的封锁,镇海口成为海上重要的对外通道。大量重要战略物资在英法控制的上海租界下船,经海路运到镇海口,再用驳船运上船,再经陆路进入浙江内陆的金华等地,再运往抗日前线。
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一定是日军攻击的目标。为了防止日本船只进入珍海口,唯一有效的选择就是封锁航道。就像当年在江阴河上封路的“元常论”一样,
在镇海口待命的“太平船”比“源昌轮”更受关注。这是因为宁波人拥有的这艘江海货轮有一个不寻常的因素。它从它的出生地上海出发,来到它主人的故乡,又会回到这里的大海,就像一个漂泊多年的流浪者,在黑暗中响应神灵对他的召唤,在晚年离开。
在上海,人们对“太平船”的不同关注记录在一份杂志上:“招宝山下的船,进出早已布满重重障碍。梅花桩填满了沉船与帆船之间的缝隙,整条封锁线如同铁桶,却空着大嘴,往来于上海与宁波之间的船只,由我们的引航船引导,驶进邕江,驶向宁波。来往船只和梭鱼一样多,货物在这里得到流通的机会。但是,码头上总有一艘巨大的船‘太平’停泊着。太平轮已经停在码头了。人们走来走去经常看到它散发出浓浓的黑烟。这艘船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下沉并封闭港口,但是已经过了这么久。印象留在镇海人眼里。”
1939年6月,准备在镇海登陆的日军开始了对镇海和宁波的新一轮轰炸。根据《宁波市志》的记录,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内,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动51架次,在镇海和宁波市投下300多枚炸弹。炸弹爆炸时刺鼻的烟味使镇海海口的防御空前紧张。
(十二)
1939年6月那些闷热的夜晚,海口镇以南20公里的东钱湖,以及旁边的小山村关颖村,犹如取之不尽的山涧,源源不断地涌入陈舜同的梦里,似乎唤醒了他心中所有对家乡的牵挂和回忆,共同迎接“太平轮”最后时刻的到来。
6月28日,太平船船长同时收到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指示击沉太平船,另一份电报是陈顺从上海发来的。太平船的船主要求船长将船的船头指向他的家乡东莞英壮。

晚上8点,朦胧的夜色中,“太平轮”发出长长的哀鸣,轰隆隆的马达鸣响,推着“太平轮”庞大的身躯,缓缓驶离招宝山下的镇海港。
江面无语,邕江之夜如此苍老,江风
夹带着阵阵燥热在空气中流动,灰暗的烟雾从“太平轮”黑色的烟囱冲出,慢慢向四周飘散。或许,“太平轮”真的有点不舍,在开阔的江面上,它笨拙、慢慢地转着身,用劲力量才画完了一个圈,无奈地向自己曾经42年的岁月作最后的告别。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江水从未经历过如此轰轰烈烈的悲壮,它以缠绵、激烈、妩媚、险峻等各种顾盼生姿的汹涌和奔腾翩翩起舞,与“太平轮”紧紧相拥在一起,似乎要用心刻录其雄壮伟岸的身影,默默地为其建起一座永恒的水上丰碑。
“太平轮”的身影终于定格在甬江口的船道上。刚健的江风迎面而来,船长紧握船舵,将船首徐徐调整朝向正南方。汽笛再次拉响,呜咽声飘散,消失在天水相连的空寂。
沉船的命令下达,船员用力拉起了“太平轮”的水底门,瞬间,白色的江水哗哗地冲进来,很快将底舱淹没。接应的小船已在“太平轮”边上等候,将要弃船离开的船长和水手站到甲板上,一阵湿润从船长眼里涌出,他把右手伸到额边,向“太平轮”送上最后的致意。
在这样一个暗色的夜间,在千年江风的见证下,42岁的“太平轮”缓缓但决绝地下沉,不断泛滚的江水拍击着“太平轮”的一侧,用这种一种激烈的亲抚与它告别,为其唱响最后的哀歌。
凌晨时分,“太平轮”的桅杆露出水面,好像一头经过奋勇搏杀的巨兽,在悲壮的倒地瞬间,把它最后的一声嘶吼留在了这个世间。
(十三)
“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当年,在飘忽的油灯相伴下,白居易用这样的诗句,追忆着其曾经拥用的温馨和感伤,所有的过往,无论是高居庙堂笙歌红袖的晕眩,还是流落江湖流离失所的艰难,在这个记忆里都成了恍如隔世的虚幻。
不知陈顺通是否读过香山居士的这两句诗,但无论怎样,这个曾在上海滩书写了无限风流,看尽了人间悲喜荣辱的宁波人,一定曾默默地坐在福熙路寓所的客厅,听着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在昏暗的白炽灯下梳理那些远去的岁月的轨痕,好像刚刚经历了搏杀的狮王正在舔拂自己的伤口,东钱湖湿润的晨雾,三江口不息的潮汐,大运河袅娜的水色,黄浦江浩荡的波浪,江阴航道湍急的江流,镇海口如雷的涛声,都幻化融合在一起,正朝他奔涌而来;那挥之不去,在其眼前时时闪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源长轮”和“太平轮”的清晰影子,像万花筒一般,不断地拼接出或艰辛或暢快,或酸楚或辉煌的画卷,在他面前一圈一圈地展开、变幻。
相关阅读
版权声明: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和用户投稿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标签: #海口花满溪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