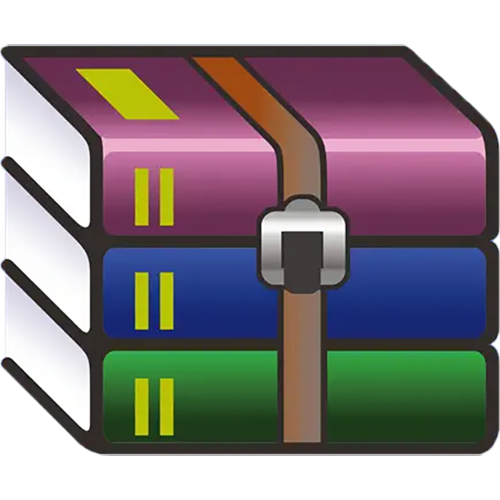混沌笼统而又无所不包的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具有巨大的应变能力与稳 定性,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解释自然现象的基本理论框架,致使中国的传统哲学 始终未能将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然作明确的划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哲学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离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 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 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①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是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深入发展的要求的,如果在以后历史的发展中未能及时让 步于精深细致的自然哲学,就会出现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曲折。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统一在一种有机网络之中,充分肯定人与 自然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但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低的古代,人与自然的 相互作用中,人始终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所谓“裁成天地之象,辅相天地之宜” “先天而天弗违”等思想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能听命由天。这样 就容易造成人们既坚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可能将自然现象与人分离而单独研究, 又感到自然难以深入理解,认为掌握自然规律是超越人类的能力的。《系辞上传》 虽然主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但又认为“阴阳不测之谓神”。孔颖达解释说: “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灭,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直到宋 朝的朱熹在研究“大衍之数”中遇到困难时,仍然无可奈何地宣称,那是“出于理 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甚至到了明朝的数学家程大位,他明知圆 周率“径一周三”只是约数,其精确值带有小数。他却认为,整数和小数的接合 处,正是“阴阳交错而万物化生”的地方,并据此得出结论,圆周率的小数部分是 “上智不能测”的。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造成人们对自然现象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恶性循环。
第二,天人合一的思想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关系纠结在一起,统治者便常常为了 人事的需要,假天命以行人事,用行政的力量强调尊崇某种思想,并把它推广到自 然科学的研究中,希望科学研究与政治人事服从统一的模式。他们希望某种模式能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盛唐时期有一次预测的日食未能出现, 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并不是先追查天文官员测算的错误,而认为是皇上的圣明引起天 人感化的结果,因而上表祝贺。张九龄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为部下推卸责任或者奉 承皇帝,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像张九龄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一代名臣,竟然能 以它作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解释日食未能出现的原因,必定是以深刻的思想文化根 源,即天经地义的“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的。
第三,天人合一的说法在实践中并不完全符合科学,将这一观点指导科学研究, 往往引出十分荒谬的结论。试看崇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汉朝人,是怎样研究动 物分类学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节 (指骨节)。”编定于东汉的《大戴礼记》中《本命》一篇更说:“有羽之虫三百六 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 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保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这是当时的动物分类学,它把所有的动物分为 羽虫、毛虫,甲虫、鳞虫、保(即裸,无羽、毛、甲、鳞者)虫五大类,每一类又 都分为三百六十种。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做法,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占据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无疑是影响中国古 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版权声明: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和用户投稿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